「法國人對法語滿心偏執?」
歷代以來,從英倫海峽北邊到訪法國的遊客,對這場景實在熟悉到讓人淚崩。劇情通常是這樣。
這位英國遊客會識相地以生疏、但或許還能讓人聽得懂的校園法語,竭盡所能地點一杯café au lait(咖啡歐蕾)或verre de vin rouge(一杯紅酒)。但是高盧侍者為了阻止他或她的這番嘗試,最典型的反應就是先冷笑一聲,再火速地把對話時的語言頻道切換到通常帶有厚重法文口音的英文。對人在法國的異鄉客而言,原本試探性朝莫里哀語言進軍的企圖,很容易因為這種傲慢回絕敗興而歸,使得有太多住在法國的英國人乾脆放棄與在地人溝通,只與外籍人士往來。想當然,法國人又能趁機抱怨英美人士「懶得說法語」。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法國人在對自己的語言以及法語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驕傲自尊、倨傲自大的同時,也潛藏著不安全感,這種糾結由來複雜。在這個議題下,我們不該忘記(因為法國人從未忘記)莫里哀的語言曾經、一度是西方世界的統治政府、階級、與文化使用的主要語言。從手段狡詐殘忍、但被一些人譽為史上首位外交家的黎胥留樞機主教統治時期到二十世紀中葉,法語曾是國際外交的通用語言。從現今世上常見的大量法文外交術語,諸如「accord—協議」、「attaché—隨員」、「aide mémoire—備忘錄」、「communiqué—公報」、「entente—協商」、「détente—緩和政策」、「chargé d’affaires—臨時代辦」等不勝枚舉,便足以證明這點。傳統上,法語主宰了各種文化與藝術領域,成為最崇高精緻品味的同義詞。
舉例來說,烹飪的大千世界裡各種高深莫測的名詞、包括「cuisine—烹飪」這個字本身,都是來自法文;古典「ballet—芭蕾」也是。也許是為了維護與統治階級的權力關係,法國歷史上一直對保存法語的純粹性這件事展現狂熱的偏執。早在一六三五年,黎胥留樞機主教就成立了特別用來規範與保護法語的國家級單位,也就是如今仍安在的法蘭西學院。法蘭西學院由四十名智慧權威的「Immortels—不朽者」組成,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規範法語純正的使用方法(雖然基本上它只能提供意見諮詢,並無法律效力)。為達此目的,學院會定期頒布篇幅龐大的《法蘭西語言辭典》之新版本;這本至今修訂到第九版的大辭典,讓院中的不朽者在過去二十年來朝經暮史地埋首書卷堆裡。自從法蘭西學院成立以來,有超過七百位群英薈萃一堂,登上不朽者名榜。他們都是政治、文學、哲學與藝術各界的無雙國士;而在這群人當中,卻僅有六位女性。不必說也知道,法蘭西學術院從來都不是一個力圖激進或創新的機構法蘭西學院在二〇〇三年曾引發議論紛紛,它不准法國人使用「email」這個字,原因是它太像英文。學院進一步宣稱,加拿大法語中的「courriel」才是最正確的法語字(滑稽的是,純粹主義者通常瞧不起加拿大法語,批評那並非正統法文)。法蘭西學院這道口頭命令頒布後,法國文化部立刻一搭一唱地跟進,禁止所有官方文件使用「email」。但這什麼用處都沒有;大多數法國人照樣「mail」來「mél」去,從不用「courriel」。許多廣告商為了配合都蓬法的規定,翻譯了廣告中的非法語字,只能硬著頭皮使用法式英語。結果,都蓬法成了全國笑柄。
事實上,法國人執著於法語應當「純粹」且「正確」的論點,正是帶它走向覆滅的原因。法國語言沙文主義已費盡太多唇舌申辯為何法語無法成為現今國際貿易語(畢竟它曾是世界通用的外交語言)。蕭伯納曾調侃說,「英語最容易講得一口破爛。」英語整日在世界各地的會議室、旅館與餐廳中任人宰割也沒人在乎,因為只要能相互了解,就算無法正確分辨現在簡單式或現在進行式、或無法在字詞間適當省略音節、或帶著厚重異國腔調,又有何謂。但法國人不然,他們總在你的發音不像教科書那般精準時出聲糾正你,而且樂此不疲。他們總習慣告訴你比起英文,法文是多麼難以精進、而且又是多麼豐富的語言(問題是英語詞彙量比法語多出五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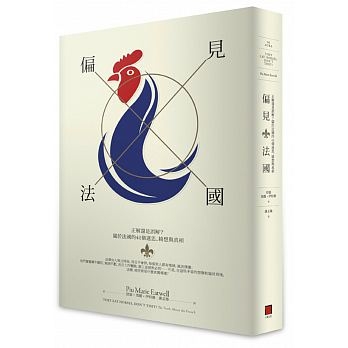
本文摘自八旗文化《偏見法國:正解還是誤解?關於法國的41個迷思、綺想與真相》



















